冰逸的《囙:黑光》:用绘画对抗身体的规训
时间:2016-09-12 来源:雅昌 作者:雅昌

“今天,仍然注重文化意义的艺术通常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它与由易逝的当前组成的周围世界保持距离,回到它自己的历史和神话之中;要么,它把大众文化的签名变成抗议或富有诗意的变形的题材。”(汉斯·贝尔廷)
冰逸选择了中国传统的纸、笔、墨,也就选择了面对中国画“自己的历史和神话”。所以,在她的纸上,预先就有了中国传统绘画从古至今的总体——对于这一总体,我们可以随口说出无数令人神往的名字。面对这一中国传统绘画的总体,冰逸首要的任务必然是充分的研究与浸泡,不是技术上,甚至不是在视觉内容上,而是在感受性上。这一研究作为中国传统画家的必修课是从什么开始的,我们在此不予追究。我只想由此选择一个最基本的切入点,即,她的绘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关于中国画的绘画,是关于中国审美感受的绘画,也可以说是某种“元绘画”。


我们还是简单地描述一下她的作品的视觉呈现:大尺寸,横幅,长卷,宽30米(有的更宽),高5米。笔墨密布,各类繁杂的(非)物象像奔涌翻滚的浪涛一样,“气势撼人”。不管她以什么标题命名自己的这类作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非)物象都以一种极具感觉冲击力的形态呈现在观者面前。冰逸说,“我的作品是写实的。”我们来看看,她写的是什么实。在近200平米的宣纸平面上,我们能看到:大片寂寥的冰川,许许多多列队站立的中古植物,许许多多盛放至高潮的大瓣花朵,大片大片澎湃的浪涌,无端陷落的地层,水蚀的地貌……我们如何理解她所说的“写实”呢。
我们发现,她作品中的物象跟我们所说的传统中国画上的形象完全没有共同之处,无论是物象的具体形态,还是象的排列组合,都跟我们印象中传统的“山水”“花鸟”等,毫无共同之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她的绘画是关于中国画的?”
2
如果简单一点,我们可以说,她所有这一类作品,总是以类似这些形态在不同的宣纸平面上,作不同的组合。根据她想要的主题,她会作出相应的明暗处理。同时,偶然与直觉也受到了充分的尊重。亮处,让我们如同在枝柯罩顶的丛林里,如同在荒寒寂寞的冰蚀高原上;暗处,甚至要深入地下岩层深处,深入到我们自己的肺腑内脏里。
把如此繁复的物象,统摄到一个个近200平米的平面上,而物象的形态又绝不重复,并且让观者觉得如同面对一江之水一样的自然,这需要某种对视觉结果的坚定与气魄。从这个角度说,冰逸让我想到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他们所有的作品几乎可以看作一件作品,但实际上又件件不同,它们占用的艺术家个人历史的时间不同,由此所涵纳的艺术家的呼吸、情绪乃至自然的天光日影都有微妙的差异。跟冰逸作品的尺寸相比,波洛克要驾驭的面积,似乎难度要小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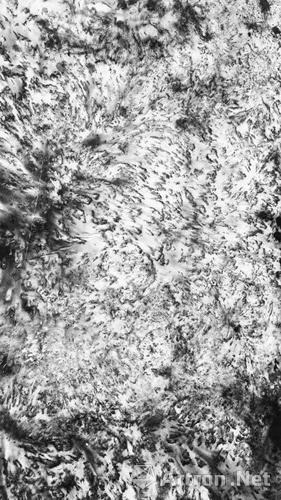
既然把波洛克牵扯进来,我们就对他们的作品作一比较。横卷(其实横竖颠倒都可以),大尺寸,总体而言的非具象,遮天蔽日式的笔墨充塞……这些都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波洛克的颜色之间的缝隙,与颜色本身同构,是明晰的感觉的游走,这个感觉没有对象,只是感觉本身,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画画的是遍布全身的神经。他的作品不大让我们联想到自然的意韵。

冰逸的作品没有颜色,她用水墨,黑白,她构像的目的是为了造境,她的像是境里的像,是经过境的折射与浸泡的像。她造的境,是中国传统绘画总体(中国绘画全集)所给予她的境,这个境与山水的幽深曲折有关,与花朵在暗夜里绽放有关。这个境不可居,只能游,是老子与庄子的游,是超越于感觉之上的精神的游。如果说布洛克的作品是属于“神经的”,冰逸的画则是属于血液的。
冰逸的作品在墨色形象中间,也有白,但这个白不同于中国画传统意义上的白,不是用来呼吸畅游的白。她作品中的白,是象的一部分,是象的补充。
所以,波洛克是西方的。而冰逸,是中国的,是关于中国的,她所做的,是中国审美精神的再生产,而非视觉现实(内容)的再生产。
3
所以,我们需要从自己的传统来关照她的作品。
如果从所有的作品几乎都使用了相似的视觉形态这个角度上说,冰逸与20世纪中国画大师之一的黄宾虹做了同样的工作,即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所有的作品或许都只是一件作品;而所有中国从古迄今的画家,极端地说,他们也只是在画同一件作品。这件作品从古至今,一直在不断地生成。这在黄宾虹身上尤其有着典型的体现。黄宾虹毕生都在画同样的山水树石,所以,我们不能像其他中国画家那样,一下子说出他有什么代表作,像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奚我后》,像傅抱石、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像吴冠中的《玉龙山下丽江城》……我们不知道哪一件作品是黄宾虹的代表作,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代表作,也都不是。黄宾虹毕生在寻找和体会的,其实是山水树石的哲学本质。黄宾虹用笔不用墨,他毕生都是在写山道石道水道树道,其绘画现代性体现于此,也止于此。

而冰逸所做的,也是在不停地寻找一种她梦想中的中国画的精魂与本质,某种道。她在接近物象的时候又及时止步,或者用一个个接续不断的象来冲淡和消解前面的象。
为此,她需要同中国画的所有绘画事实、绘画形象与意象斗争,同时又要接受它们的精神诱惑——这一诱惑潜隐铭刻在中国传统的所有文学与艺术与事物中,从而,来建立自己的当下与此时此刻性。这一当代性同时也与以西方当代艺术为资源的方力钧、刘小东、张洹、曾梵志等艺术家的当代性形成一种时代同构关系;后一种当代性,我们似乎可以确定,就是汉斯·贝尔廷所说的另一个“要么”。

这另一个“要么”,现在已经处在让·波德里亚所说的“纵欲狂欢之后”。“纵欲狂欢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呢?冰逸所选择的“要么”,相对于八五新潮之后至今的当代艺术家以西方艺术为观念资源的另一个“要么”来说,也许是从我们自己出发,再次往另一种“纵欲狂欢之后”进发的一个路径选择。
4
从画面尺幅所体现的雄心与抱负来说,冰逸的作品可以说是精神分析版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里的江也好山也好,都是写实性的视觉呈现,但实际上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因此可以说,王希孟是在表征他心中的抽象的山水精神。
王希孟和黄宾虹的作品从视觉进入,然后同时拍击所有的感官,拍击“没有器官的身体”。
冰逸的作品从视觉进入,然后组合各种感官:内视觉,触觉(手的、皮肤的),听觉;她用画面上的所有信息来重新组织身体的各种感官。
所以,不必感到奇怪,冰逸的作品同时给我们如下的感觉:花在暗夜里绽放的声音,地壳沉降的眩晕,惊涛骇浪的呼啸,地下岩层的深邃与探索,以及我们自己身体内部的奥密……
听觉,视觉,触觉,嗅觉,手,脚,皮肤,身体……冰逸一次次地邀请我们把自己都投进去,乃至让我们像撕开上衣的纽扣一样撕开自己的身体。
5
著名摄影师焦恩·迈利(Gjon Mili)曾为毕加索拍过一系列光绘画摄影作品:毕加索拿着荧光棒在摄影师面前的空气中作画。光线的运动创造出了我们在纸上常见的《和平鸽》那样的毕加索式立体派线描作品。
摄影师的作品能引发我们什么样的哲学或美学观念思考,我们在此不作尝试,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家在完成一件作品的整个过程中,他(她)的身体的运动与作品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即他(她)的身体在创作一件作品时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属性,这种属性对于他(她)的作品的美学(艺术)品质有没有影响,如果有,那么这是种什么样的影响。(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以祝枝山的身体为笔作了一幅《雄鹰展翅图》,对于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而言,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舞者用文化驯化身体,运动员用技术训练身体,而画家用画笔牵引身体。

我看过张大千作画的录像,宣纸摊在案上,张大千手持毛笔,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眼睛始终凝视在画幅的尺寸之内,笔与纸接触时的阻力感,不停地催动情绪持续与走高。他的身体的运动范围基本在一两平米之内,脚下生根。他作画时的身体运动,是文化规训之后的运动。
我见过马蒂斯站在画布前作画的照片,一手持一两米长的画笔,眼神专注,人进入灵视状态,也是脚下生根,整个人宛如山岳。他作画时的运动,也是具有文化的规训性。
泼,抹,擦,勾,刷,点;用笔,用刷子,用桶,有盆;或就,或离,或迅疾,或凝滞,或迂回……我很好奇冰逸在作画时的身体运动,要知道,她的作业平面经常有数十平米。她的脚是移动的,她是内视点。她不是多视点,而是移动视点。
她是用文化规训的身体,来反抗身体的规训文化,那么,她的结果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身体平行于作品,让作品同时成为一个身体,“没有器官的身体”,也即是去权力秩序化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