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沂 | “语-图”之辨与西方当代艺术写作(下)
时间:2018-01-12 来源: 西西弗斯艺术小组 作者: 西西弗斯艺术小组
前文推荐:
诸葛沂 | “语-图”之辨与西方当代艺术写作(上)
三、“语-图”关系认知的当代艺术写作实践
理论界的探索总是高屋建瓴的,但也总有凌空蹈虚之嫌。因为一旦要将这种跨越“语-图”之辨的图像理论运用到具体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的对象性写作中时,老问题又出现了,语言总是会再次侵入图像,图像又照样固若金汤地坚守着堡垒,要解决语言与图像之间的砥砺与龃龉,就必然期待一种具有批评性、可行性的解读方式。考察近几十年的艺术写作,许多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直接受到了利奥塔、巴特、雅各布森和皮尔斯等的影响,尝试了这一挑战,奉献了许多重要的艺术写作文本。
1.“语-图”互惠:迈耶·夏皮罗与《语词与图画》
被誉为“美国艺术史教父”的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 1904-1996)学术成就斐然。这位享有“传奇人物”之名的杰出艺术史家既是罗马艺术和中世纪艺术的专家,又写作了大量论现代主义和他当时的当代艺术的文章。夏皮罗的学术成就一般被认为体现在其四卷本的选集中:《罗马式艺术》、《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古代晚期、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艺术》,以及《艺术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近来,第二本和第四本已由沈语冰教授及其翻译团队译出,这填补了我国西方艺术史学研究领域的一段空白。
夏皮罗的艺术写作受到当时广阔的知识分子文化氛围的影响和塑造,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激荡的思想和理论冲刷着笔端,也促长了他作为一位严肃的艺术史家和敏锐的艺术批评家的写作高度和复杂性。他既反对那种对于作品进行的居高临下的、单一排外性的图像学分析,也曾严厉地批评那种对于现代艺术的纯粹形式分析。他曾抨击纽约MoMA的第一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因为后者在为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的划时代展览所撰写的展览目录中运用形式主义方法来分析抽象性,他却宣称,伴随着历史情境,抽象艺术是意义深长的,比如俄国前卫艺术那凌厉的、技术性的风格,恰恰证明了一种对机器解放力量的确信信念。[1]在《塞尚的苹果》(“The Apple of Cézanne”,1968)一文中,夏皮罗反对塞尚的形式主义分析惯例,发展出一种针对画中苹果特殊位置而进行的准-精神分析解释。[2]夏皮罗的抱负,是要在图像学和形式主义之间找到一条途径,超越那种将视觉图像要么赋予常规意义、要么判定为无意义抽象的思维定式。

迈耶·夏皮罗:《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沈语冰、何海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
夏皮罗在论文《视觉艺术符号学中的某些问题:图像-符号的场域与载体》(1969)和著作《词语和图画》(Words and Pictures,1973)中,都试图通过将焦点转向图像的非模仿方面(nonmimetic aspects),质疑(problematize)图像学。在《视觉艺术符号学中的某些问题》中,他把研究限定于“图像-符号中的非模仿性因素及其在符号建构中的作用”[3]这个范围内,其中包括画面未经处理的表面、边界和边框、摆放的位置和方向、作品的形状以及图像实体的质量等符号表征和物质特征上,从而避免绘画的形式传统和再现性等问题。他要探究的,是“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任意的,在多大程度上又存在于图像制作与图像感知的有机条件中”,[4]比如画框在构成符号意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边框也能进入图像的形塑,在现代风格中,通过用边框切割前景中的对象,边框似乎穿过了一个在后面伸展的再现场域;德加和劳特累克是这类图像的天才大师。[5]贯穿整篇文章,夏皮罗通过案例,展示了图像的非模仿性的、非图像学的方面,给我们理解这些图像施加压力。
在《词语与图画》这本小书里,夏皮罗再次将绘画的意义场域扩充到非模仿性的画作元素上。他论证道,一种对圣经故事的描绘并不仅仅再现了文本;相反,赋形改变了故事,并且,实际上,它为后来的文本详述构建了基础。虽然图像可能会把故事化繁为简,但它也会扩大文本内容,添加细节形象,甚至放上原文里没有的东西。[6] 正如法国艺术史家于伯特·达弥施(Hubert Damisch,1928-)所观察到的,夏皮罗所支持的,是文本与图像的互惠关系。[7]夏皮罗这些文字所累积的效果,便是通过符号学为词语和图像建立共同基础,从而缩小它们之间的距离。[8]
2.形式无观念:伊夫-阿兰·博瓦和罗莎琳·克劳斯的“无形式”(Formless)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罗莎林德·克劳斯(Rosalind E. Krauss,1941-)和哈佛大学教授、符号学家伊夫-阿兰·博瓦(Yve-Alain Bois,1952-)便开始尖锐、持续地攻击现代主义盛期的格林伯格式的形式主义叙事和艺术史分类学。1996年,这两位批评家在巴黎蓬皮杜中心策划了一场名为“L’ informe: mode d'emploi”(无形式,英文formless)的展览。这次展览及其展览目录,应被看成是对既有现代主义艺术史叙事及其价值评价标准的激进批评,在他们看来,以现代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极度科学化”、“分析性”、“理性/感性”、“形式/材质”等二元论的观看方式,对艺术创作本身充满了伤害。而“非形”这个概念,则是一个消解既有概念、模糊概念之间的边界的过程。

Bois, Yve-Alain and Rosalind E. Kraus. Formless: A User's Guid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7.
“无形式”一词直接来自于超现实主义批评家、诗人和哲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的著作,后者是克劳斯和博瓦策划这次展览的关键推动力。巴塔耶认为,宇宙便类似于无形,像蜘蛛和唾液一样。[9]他借“无形式”来反对形式美学,否定再现;而克劳斯和博瓦则借巴塔耶的反叛精神来反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反击现代主义对“无形式”的误读。[10]
博瓦认为,现代主义原初状况的运作(operation,同样也是巴塔耶论著里的一个重要术语)正是“无形式”的,而非依据后来现代主义形式理论而生成,同时,“无形式”也不具备确定意义,它只是一种“运作”,没有确定的图像学意义;它只注重过程,不以再现、主题和观念为预期目的;它只是一个消解既有概念的过程,它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无形式”的运作打破了旧有的分类法,成为了一种“反升华/反崇高的攻击行为”(“desublimatory act of aggression),[11]这种行为需要一种对“卑俗”(“base”)物质的暴露,如唾液,便是对既有等级制的抵抗,因为它们具有(反-)形式品质的倾向,它们还有不和谐、不确定的轮廓,以及不精确的着色。[12]这种“卑俗唯物主义”(base materialism)观念[13]所强调的,正是形式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跟随“无形式”的思路来看,形式不再是观念的承载物,甚至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区分也不存在了,既然如此,力图解释形式-观念机制的论述和图像学,都是自大而徒劳的。
3、反符号学:吉尔·德勒兹的《弗朗西斯·培根: 感觉的逻辑》
《弗朗西斯·培根: 感觉的逻辑》是法国现当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以哲学触探绘画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德勒兹富有创见地指出,除了具象和抽象之外,现代绘画还有第三条路线,那就是用一种具有触摸能力的视觉取代纯粹的视觉,重新建构起古埃及和古希腊艺术中的“触觉-视觉”空间——而这个“美妙统一体”[14]曾多次被打碎,依靠着塞尚开始的某些卓越的艺术家,这个空间才得以在画布上重生,弗朗西斯·培根亦是其中之一。
德勒兹在此书第一章《圆,圆形的活动场所》里就引用培根的话评价他的三联画:使用三块孤立的画板拼装而非汇集到同一画框的原因,“是为了驱赶走形象中的‘具象性’、‘图解性’和‘叙述性’……绘画既没有需要表现的原型,也没有需要讲述的故事。”[15]要回避具象性,躲避被解释的命运,绘画就只有两条路,一是达到纯粹抽象,二是抽取或孤立出纯形象性。培根显然是属于后者——通过形象孤立,他的画作与表现决裂、打破叙述、阻碍图解性的出现,从而解放形象:只坚持绘画事实。[16]
德勒兹在讨论培根的著作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培根的艺术中,感觉是如何呈现为形式的?他认为,培根的艺术道路,是遵从肉体/感性的感觉逻辑,即通过对“纯形象”的追求,以及对手工性的“图形表”(diagramme)的把握和运用,最终达到同一种全新的视觉:触觉般的视觉——一种更加直接、更加感性的绘画。它回避了形象化和叙述性,打破了符号规划,使形象得到解放。
德勒兹的艺术写作,实际上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艺术化的哲学和哲学化的艺术,共同构成了一种思维和表达方式的文化转型。但是,他在打破符号学在艺术写作中的霸权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种哲学化写作霸权。显然,“语-图”之辨仍然没有最终得到超越。
4.反思与超越:T.J.克拉克与《瞥见死神》的写作实验
当代艺术社会史家T.J.克拉克(T. J. Clark,1943-)作为欧美“新艺术史”的领军人物,以其艺术社会史研究而著称于世。从早期作品《绝对的资产阶级》《人民的形象》和《现代生活的画像》,到1999年出版的《告别观念》,克拉克始终强调艺术是社会进程的一部分,通过艺术惯例的改变而折射出社会,同时,艺术对社会具有能动作用,他还将现代主义界定为以极端的艺术试验隐喻性地抵抗资本主义总体性的艺术乌托邦运动。尽管他的现代艺术史研究自成体系、影响极大,但也遭了诸如“自大”、“武断”、“观念先行”、“黑格尔主义”和“不尊重图像”等批评。为了廓清形象,给自己辩护,克拉克在2006年出版了《瞥见死神:艺术写作的一次试验》(The Sight of Death: An Experiment in Art Writing,2006),其超越“语图之辨”的写作,既颠覆了学界对他的刻板印象,又为当代艺术写作树立了新的标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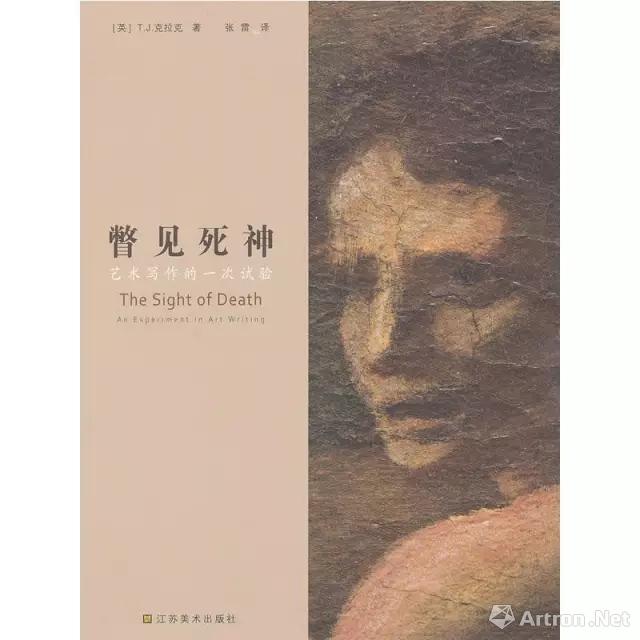
T.J.克拉克:《瞥见死神:艺术写作的一次试验》,张雷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2年。
克拉克用日记体与谦逊的修辞,记录了自己对两幅普桑画作的每日静观及深刻体验,他不再关注意义,注重绘画物质性品质,把重点放在思索观看的方式及其效果上:“我”从画里接收到了什么,时间如何改变观看,变化的光线如何改变图画本身……等等。这种共时性写作方法集绘画、观看和书写于一体,既挑战了那种围绕某个哲学、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主题而阐释的传统写作,又没有掉进先前被人误解苛责、留下刻板印象的艺术社会史写作模式之中。[17]
他发现,一旦以天真的眼光去细看画作,作品便“不能全然化为一种可自如使用的阐释性叙述。[18]所以,他运用准-自动的、碎片式的、开放性的、以过程为导向的方式来进行写作,他希望这能在某种程度上效仿真正的视觉图像的非线性的、晦涩而不透明的特性,他希望借此揭露并尊重言语和视觉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克拉克直率的表述:“图像绝不能彻底脱离文字,不能彻底摆脱演讲的挚制,但图像有能力且意欲探索出符号与姿态,或者系统性结构与物理性(视觉性,质料性)间隔之间的区别”。[19]
《瞥见死神:艺术写作的一次试验》的写作试验既实现了“语-图”之争的和解,达到了艺术与语言的共鸣;又从根本上对那种脱离社会现实、忽略图像静观、标榜新颖理论、沦陷于不断膨胀的资本主义总体性及文化工业的“异化”的艺术写作现状进行了批判,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指出了超越“语-图”之辨的艺术写作新方向。
本文原载于《美术研究》2017年第1期,欢迎转载,如需转载请说明出处。
作者简介:

诸葛沂,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艺术史、艺术哲学和艺术批评研究。







